寄栎园少司农兼送雪客归金陵
读画高楼几千尺,楼阴下枕清溪碧。面揖南朝无数山,四时云气生虚白。
先生卷帘楼上头,独立看山自朝夕。平生好诗兼好画,尤爱图书与金石。
购买不惜倾家赀,尽是前人好手迹。山川患难不肯离,始信先生有真癖。
早年事业多恢奇,许身管葛千人辟。已树羊祜山头碑,再掌萧何府中籍。
岂意青蝇飞满眼,遂教白发垂过额。匹马来看岱岳云,一官又返钟山宅。
风涛宦海理有之,何用呶呶骂门客。有书可读诗可吟,万事徒劳挂胸膈。
人生甲子休浪过,如此朱颜亦堪惜。世情翻覆原转环,况复长安事如弈。
我别先生江水头,相逢令子燕山陌。执手问讯何所为,却道高怀胜畴昔。
雄夸酒赋老益神,傲兀林泉意多适。侧耳令我发狂叫,自顾胡为苦偪窄。
此身一陷泥沟间,巢鷇何能奋毛翮。君归道我语家尊,行路崎岖半蜂螫。
心有㦷气口直言,那怪腾轩遭贬斥。不如且酌春江万斛水,高筑糟丘酿仙液。
好待吾徒醉百场,千秋万世名何益。
汪懋麟[公元一六四o年至一六八八年]字季角,号蛟门,江苏江都人。生于明思宗崇祯十三年,卒于清圣祖康熙二十七年,年四十九岁。康熙六年(公元一六六七年)进士,授内阁中书。因徐乾学荐,以刑部主事入史馆充纂修官,与修明史,撰述最富。吏才尤通敏。旋罢归,杜门谢宾客,昼治经,夜读史,日事研究,锐意成一家言。方三年,遽得疾卒。懋麟与汪楫同里同有诗名,时称“二汪”。著有百尺梧桐阁集二十六卷,《清史列传》行于世。
天台生困暑,夜卧絺帷中,童子持翣飏于前,适甚就睡。久之,童子亦睡,投翣倚床,其音如雷。生惊寤,以为风雨且至也。抱膝而坐,俄而耳旁闻有飞鸣声,如歌如诉,如怨如慕,拂肱刺肉,扑股面。毛发尽竖,肌肉欲颤;两手交拍,掌湿如汗。引而嗅之,赤血腥然也。大愕,不知所为。蹴童子,呼曰:“吾为物所苦,亟起索烛照。”烛至,絺帷尽张。蚊数千,皆集帷旁,见烛乱散,如蚁如蝇,利嘴饫腹,充赤圆红。生骂童子曰:“此非吾血者耶?尔不谨,蹇帷而放之入。且彼异类也,防之苟至,乌能为人害?”童子拔蒿束之,置火于端,其烟勃郁,左麾右旋,绕床数匝,逐蚊出门,复于生曰:“可以寝矣,蚊已去矣。”
生乃拂席将寝,呼天而叹曰:“天胡产此微物而毒人乎?”
童子闻之,哑而笑曰:“子何待己之太厚,而尤天之太固也!夫覆载之间,二气絪緼,赋形受质,人物是分。大之为犀象,怪之为蛟龙,暴之为虎豹,驯之为麋鹿与庸狨,羽毛而为禽为兽,裸身而为人为虫,莫不皆有所养。虽巨细修短之不同,然寓形于其中则一也。自我而观之,则人贵而物贱,自天地而观之,果孰贵而孰贱耶?今人乃自贵其贵,号为长雄。水陆之物,有生之类,莫不高罗而卑网,山贡而海供,蛙黾莫逃其命,鸿雁莫匿其踪,其食乎物者,可谓泰矣,而物独不可食于人耶?兹夕,蚊一举喙,即号天而诉之;使物为人所食者,亦皆呼号告于天,则天之罚人,又当何如耶?且物之食于人,人之食于物,异类也,犹可言也。而蚊且犹畏谨恐惧,白昼不敢露其形,瞰人之不见,乘人之困怠,而后有求焉。今有同类者,啜栗而饮汤,同也;畜妻而育子,同也;衣冠仪貌,无不同者。白昼俨然,乘其同类之间而陵之,吮其膏而盬其脑,使其饿踣于草野,流离于道路,呼天之声相接也,而且无恤之者。今子一为蚊所,而寝辄不安;闻同类之相,而若无闻,岂君子先人后身之道耶?”
天台生于是投枕于地,叩心太息,披衣出户,坐以终夕。
治平二年五月丁亥,赵郡苏轼之妻王氏卒于京师。六月甲午,殡于京城之西。其明年六月壬午,葬于眉之东北彭山县安镇乡可龙里,先君、先夫人墓之西北八步。轼铭其墓曰:
君讳弗,眉之青神人,乡贡进士方之女。生十有六年而归于轼,有子迈。君之未嫁,事父母;既嫁,事吾先君先夫人,皆以谨肃闻。其始,未尝自言其知书也。见轼读书,则终日不去,亦不知其能通也。其后,轼有所忘,君辄能记之。问其他书,则皆略知之,由是始知其敏而静也。
从轼官于凤翔。轼有所为于外,君未尝不问知其详。曰:“子去亲远,不可以不慎。”日以先君之所以戒轼者相语也。轼与客言于外,君立屏间听之,退必反覆其言,曰:“某人也,言辄持两端,惟子意之所向,子何用与是人言。”有来求与轼亲厚甚者,君曰:“恐不能久,其与人锐,其去人必速。”已而果然。将死之岁,其言多可听,类有识者。其死也,盖年二十有七而已。始死,先君命轼曰:“妇从汝于艰难,不可忘也。他日,汝必葬诸其姑之侧。”未期年而先君没,轼谨以遗令葬之,铭曰:
君得从先夫人于九泉,余不能。呜呼哀哉!余永无所依怙。君虽没,其有与为妇何伤乎。呜呼哀哉!
暂向花封陪客醉,已闻芝检促归装。昌黎宁许到潮阳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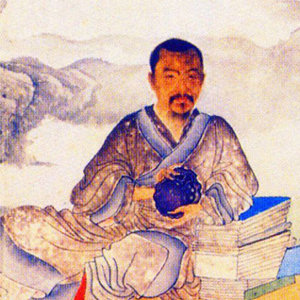 汪懋麟
汪懋麟 辛弃疾
辛弃疾 方孝孺
方孝孺 苏轼
苏轼 完颜亮
完颜亮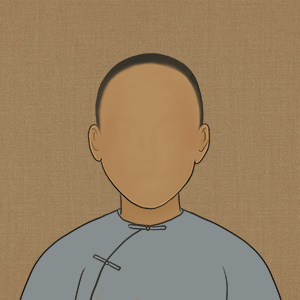 刘镇
刘镇 陈允平
陈允平 毛滂
毛滂